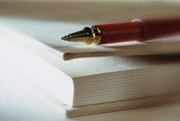转基因好不好 转了才知道
转基因水稻最近一直被热炒,说什么的都有。我今天看到纽约时报一篇非常好的报道,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转基因到底好不好?只有自己转了才知道。
事情要从2002年说起。那年有个名叫Drew Endy的32岁的科学家去了MIT,研究生物工程:
Endy是工程师出身,他发现生物工程和他熟悉的工程学相差太远了,典型的工程学很像搭积木,零部件都是现成的,工程师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组合起来而已。他想把生物工程也变成这个样子,这在早几年还不可能实现,但在2002年时时机已经成熟,他甚至在MIT还发现了几个和他志同道合的工程师,分别叫做Gerald Sussman Randy Rettberg Tom Knight
这4人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开始在MIT实践他们的理想。他们把单个细菌的基因组视为工具箱,DNA视为工具,细菌就是成品。他们设想通过基因工程的手段造出新的细菌,具备一些原本没有的新颖功能。说实话,这个想法并不新奇,但他们想出了一个前人都没有想到过的方法:利用学生们的自主能力去扩展研究思路,扩大研究范围。
他们在MIT为本科生开了一门课,布置的第一个作业就是让学生们制造一种“会眨眼”的细菌,每隔一定时间就发出荧光。这门课很成功,于是很快变成了一个竞赛,取名iGEM,就是“国际基因工程机器设计竞赛”。第一届参赛的队伍一共才有35所大学的学生团队,到今年已经有120个学校了。
这个竞赛不光是把现成的基因转来转去,而是要求参赛者对现有的基因做出改良,或者干脆自己设计一个(或几个)基因,再组装到细菌中,把细菌变成一个全新的东西。MIT负责为参赛者提供“工具”,也就是“基因试剂盒”,里面包括各种基因片段和工具箱(Kit),参赛者需要在这些“工具”的基础上设计出自己的新工具,然后组装成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说,目前大家争议很多的所谓“转基因”只是简单的复制和粘贴,而当我们还在争论复制和粘贴是否可行的时候,人家已经开始自己制造新的内容了!
如此“高科技”的东西,肯定只有高等学府才有资格参加对吧?中国就是这么做的。目前中国只有北大复旦清华和科大等少数高校参加这个竞赛,北大的团队甚至获得了2007年度的iGEM大奖。但我去搜了这方面的报道,最详细的是这篇,我仅仅看到了为国争光的信息,就连北大学生的获奖作品究竟是什么都没有提到。
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就是关于2009年iGEM比赛的,但记者选取的报道对象却是一个来自旧金山湾区的一所社区学院的参赛队伍。所谓社区学院很像我们的技校或者成人大学,上学的都是一些考不上正经大学的所谓“后进生”,或者是工作后又打算补点知识的成年人。通常学费很便宜,这所社区学院每个学分只要26美元,一般每门课也就3-4个学分,大家可以算算上这个学院需要花多少银子。
就是这样一所社区学院,居然决定参加2009年的iGEM大赛!学校经费紧张,只能提供一间屋子作为临时实验室。研究经费大部分来自一位校董从一个伯克利校友的遗孀那里拉来的1.8万美元的赞助,其余大部分仪器都是队员自己买来或者借来的。一开始学院里有很多学生参与进来,设计方案,做些准备工作。后来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一个核心团队。让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是谁:
左起:
Leeza Sergeeva,19岁,来自莫斯科的第一代移民,小组组长。
Bowen Hunter,27岁,按摩理疗师,中学上的是特克萨斯一所神学院,学的是神创论。
Angela Brock,34岁,电子工程专业学生,退学10年后重新回校读书。
Bertram Lee,47岁,曾经做过10年软件工程师,后来对生物工程发生兴趣,重新回来读书。
Colby Sandate,21岁,一半墨西哥一半意大利血统,平日的工作是卖化妆品。
Dirk VandePol,41岁,旧金山城市学院教师,也是这个团队的指导员,但他教的不是基因工程,而是“人体生理学入门”。
就是这样六个人,试图制造出一种细菌,能够利用太阳光来发电!
读到这里,你也许认为这又是一个美式的英雄故事。错。这个团队最后没能成功,甚至连参赛的基本要求都没有完成,被取消了评奖资格。最后获胜的是来自剑桥大学的团队,获奖作品是一种能够根据环境毒素的不同而发出不同颜色的荧光的细菌。可以想象,这种细菌将会对环境监测有帮助。
通过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仅靠业余科学家小打小闹,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是,这个故事又不是一个美版“民科”的故事,他们并不想通过科学出人头地,或者“颠覆现有的科学理论”,而是觉得科学好玩,很想参与进来,跟上现代科学的发展步伐而已。
我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个团队都是普通得没法再普通的人,他们有梦想,同时又肯钻研,我敢肯定他们在参赛的过程中学到了生物工程的很多知识,从此便不再对“转基因”产生盲目的恐惧。别小看来自民间的恐惧,这种恐惧实际上已经严重影响了生物工程技术在现实中的应用。
对比一下电子工程和生物工程的进展就知道了。我们对电子工程几乎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允许电子工程师犯错误,并在犯错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给生物工程这个机会,当然生物工程也确实需要采取比电子工程严格得多的管理,但有些人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要求所有的生物工程都必须证明完全没有任何错误才能应用,这个标准已经高到几乎无法实现的程度了。比如中国批准的转基因水稻转的是一个Bt杀虫基因,这种基因编码一种生物杀虫剂,已经被使用了70多年,但有些人还是觉得试验不够长,还要继续试验下去。请问究竟需要试验几千年才能让您满意呢?
转基因确实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我从目前的大部分报道中没有读出任何一个站得住脚的质疑。比如说专利问题,新技术当然要有专利,您以为科学家都是活雷锋吗?再比如抗性问题,当然会有,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应该是不断研发新的转基因农作物,而不是干脆禁止,任由农民使用化学农药,您以为化学农药就不会产生抗性了吗?
说白了,很多质疑的人都属于一提到转基因就骂娘的主儿,根本就不相信科学技术能解决问题。对比一下中美对于iGEM比赛的态度和报道方式你就知道,说到底这还是一个科普教育的问题。大部分人根本就不知道基因到底是怎么回事,更别说亲自转个基因了,所以他们才会把转基因当做洗脚水,不惜把孩子一同倒掉。如果有机会让普通人都来转个基因试试,他们就会明白,转基因没什么可怕的,它就像很多先进技术一样,都会有优缺点,只有用平常的心态来对待它,扬长避短,才能发挥它的优势,造福人类。
合成生物学指引我们向何方?
当Jay Keasling在大约10年前第一次听到”青蒿素”这个词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毫无头绪。” Keasling,这位来自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生化工程学教授如此回忆道。尽管青蒿素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治疗疟疾的药物,Keasling并不是传染病方面的专家。但他非常凑巧的参与了一门新学科的创造过程:合成生物学――结合了工程学,化学,计算机以及分子生物学――一门致力于集合必要的生物工具来重新设计这个大千世界的新兴学科。
科学家们熟练操控基因的时间已经长达几十年了;在各种各样的微生物中插入,剔除又或者改变基因,已经是万千实验室中的常规操作了。 Keasling和他那些来自全世界并且数量急速增加的同事们却有着一些更加激进的念头。他们尝试着利用基因的序列信息和人工合成DNA,去改装细胞的新陈代谢路径从而使得细胞具有全新的功能,例如生产化学物质和药品。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尝试从无到有地构建基因――以及新的生命形式。Keasling和其他人所做的是整合那些用以铸造新系统的生物因子――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并且参与创立这个领域的资深科学研究者Tom Knight将它命名为“生物砖石”。每一块生物砖石都由标准化的DNA片段组成,可以被用于创造或修改细胞。 “如果你的硬盘挂了,你可以去最近的一家电脑用品商店,买一个新的然后换上,”Keasling说,“因为它是一个按照标准而制作的机器部件。整个电子行业都以即插即用为宗旨。拿到一个晶体管,把它插进对应位置,大功告成。在一部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中可以用的零部件,在另一台中照样可以用。这个原理也同样适用于几乎所有的东西:当你去Home Depot(家得宝)买东西的时候,你不用考虑你买的那把螺栓的螺纹尺寸,因为它们全是按照统一标准制作的。为什么我们不以同样的方式应用生物学呢?”Keasling和这个领域中其他人的工作地点,分属于旧金山海湾地区和麻省剑桥市,地跨北美两端(或者说 “Keasling和这个领域中其他人的工作地点,分属于美国东西海岸的旧金山海湾地区和麻省剑桥市”)这些人视细胞为硬件,基因编码为软件,努力令这个新系统运行起来。合成生物学家相信,只要有足够的知识信息,他们可以写出控制基因组件的程序――使他们不仅可以改变自然,甚至可以引导人类演化的过程。
从来没有任何科学成就许下这样不可思议的承诺,也没有哪个科学成就曾背负着如此巨大的风险,或者有着如此清晰的被蓄意滥用的可能性。新技术所带来的好处――从转基因食品到药物学奇迹――经常会被夸大其词。但如果合成生物学成功了,他们将把特化的分子转化为可以自给自足的微型工厂,制造出便宜的药物,干净的能源,还可以造出新型生物,帮我们吸走大气中多余二氧化碳。
2000年,Keasling致力于寻找一种可以展现合成生物学工具作用的化学物质。他把目光投向了一类叫做类异戊二烯的有机分子,这类物质与和多种植物的香味、口味甚至颜色都息息相关,例如桉树,姜,肉桂,还有向日葵的黄色和番茄的红色。“有一天一个研究生过来跟我说,‘看看这篇论文,是有关青蒿酸(青蒿素前体)合酶的,’”Keasling告诉我说,那时我们正在他位于Emeryville的办公室,与旧金山隔了海湾大桥遥遥相望。他刚刚被任命为能源部新设立的联合生物能源研究所CEO,这个研究所是三个国家实验室和三个大学联合研究的一部分,以 Lawrence Berkeley国家实验室为首。这个联合组织的首要目标就是设计并且生产一种排放很少或者不排放温室气体的新型人造能源,这也是 Obama总统最常提到的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Keasling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他的学生。“‘青蒿酸,’我说,‘那是什么?’他告诉我那是青蒿素的前体,而青蒿素是一种有效的抗疟疾药。我从来没有研究过疟疾。但是我做了简要的调查,很快意识到这个前体同我们计划研究的东西同属一类。我想,青蒿酸也是一个不错的研究对象。让我们行动吧。”
疟疾每年大约会感染5亿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并且致使其中多达100万人丧生,丧生者多数是5岁以下的儿童。几个世纪以来,标准的治疗方法是使用奎宁,或者是其衍生物氯喹。由于氯喹每剂量只需10美分,便宜又简单易合成,它拯救了数以百万的生命。但是到了90年代早期,最致命的传播疟疾的寄生虫――Plasmodium falciparum(镰状疟原虫)――对这种药产生了抗药性。更糟糕的是,候补的治疗药,乙酰嘧啶磺胺多辛,或简称 SP,也大规模地失效了。青蒿素与其他药物的联合使用,就成为了唯一一种始终有效的治疗方法。(对于某一种药物的依赖会增加疟原虫产生抗药性的几率。)在西方被称为黄花蒿或者甜艾的这种草药,含有青蒿酸,在很多地方大面积的生长,但是供应量却在各地差异很大,当然,差异很大的还有价格。
对青蒿素的严重依赖,尽管是逼不得已,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联合治疗法的成本高达氯喹的十到二十倍,并且尽管国际慈善组织给予越来越多的支持和帮助,这笔钱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依然是天文数字。青蒿素的获得过程并不简单。黄花蒿一旦收获,叶与茎都必须要尽快处理,不然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有效成分会很快被破坏。产量低,成本高。
尽管几千名亚洲和非洲的农民已经开始种植这种植物,世界卫生组织(WHO)预测未来几年内的年需求量――每年多达5亿个疗程――将远远超过供应量。如果这些供应被切断,后果将是无法预料的。“没有青蒿素,我们的治疗水平将倒退至少几年,甚至几十年,”Kent Campbell,疾病控制与防治中心疟疾部的前负责人以及非赢利性医疗机构PATH疟疾控制项目的现任负责人如是说。“你可以随便设想出一些理论上的世界性公共医疗灾难。但这一次不是理论上的了,而是真实的。没有了青蒿素,数以百万计的人将死去。”
Keasling意识到如果合理利用合成生物学的工具,就可以完全不受自然条件控制,提供一个充足的新的青蒿素来源。如果每一个细胞都变成了它自己的小工厂,生产出制作药物所需的化学物质,那么就不再需要繁复且成本很高的生产过程了。为什么不试着由基因片段出发,构造一个细胞去生产青蒿酸呢?Keasling和他的团队需要拆开一些不同的生物,然后将几十种基因的一小部分分别拿出来,拼凑成为特定目标量身订做的DNA包裹。之后他们需要构建一个新的新陈代谢通路,使得细胞可以利用化学通路完成自己的任务――一个在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任务。“我们认为人类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阶段――一个我们不必再被动的接受自然所给与的东西,”他这样对我说。
2003年,这个团队公布了他们的第一次成功经验,他们在《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上发表论文,描述科学家们如何通过将三种不同生物的基因插入大肠杆菌(世界上最常见的细菌之一)中,从而创造了新的路径。这个研究帮助Keasling从 Bill and Melinda Gates基金会拿到了一笔高达四千两百六十万美金的研究资金。Keasling感兴趣的并非简单证明这门科学确实行得通;他希望将这门科学大规模应用以抗击疟疾。“生产几毫克青蒿素好比是变一个干净利落的科学戏法,”他说。“但是如果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 Berkeley的实验室里做一个精彩的实验,那么对于非洲的人们没有任何用处。我们需要把它变成工业规模的生产过程。”要把科学变成产品,Keasling协助建立了一个新公司,Amyris生物技术公司,进一步完善最初改造出的微生物,并且找到更具有效率的生产方法。10年之内,Amyris已经将每个细胞可以生产的青蒿酸的量提高了100万倍,使得每一剂量的药品成本从10美元下降到了不到1美元。
Amyris随后和旧金山的一家非营利性药品生产商美国人类健康研究所(Institue for OneWorld Health)合并,2008年他们跟一家巴黎的药品公司Sanofi-Aventis签署了一份协议来生产这种药,并且希望可以于2012年以前上市。科学界对此满怀敬意――他们的青蒿素被视为合成生物学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产品,证明了我们不需要仰自然之鼻息才能化解迫在眉睫的世界危机。但是也有一些人担心合成青蒿素将带给数千个已经开始种植甜艾的农民带来什么影响。“如果California实验室里的培养桶替代了农场,那些辛苦劳作在亚洲和东非的农民要怎么办?”Jim Thomas,ETC小组(加拿大的一个科技监督团体)的一位研究者发出了这样的疑问。Thomas指出,对这种从如此根本的层面改变自然的行为,一直以来很少人有谈论其所带来的伦理和文化冲击。“科学家们在制造从未存在过的DNA序列,”Thomas说,“所以它们不存在比照物。因此没有一个达成共识的安全体制,没有政策约束。”
Keasling也相信国家需要考虑这项技术的潜在影响,但他很疑惑,为何有人反对这种即将成为世界上最稳定最便宜的青蒿素来源的技术。“如果我们假设,现在面临危机的不是青蒿素而是抗癌药物,”他说,“并且整个西方世界都只能依靠中国和非洲的农民,我们甚至不确定他们是否将继续种植这些作物。同时很多的美国孩子都因此死去。看看这样的世界,看你敢不敢告诉我我们不应该发展这项技术。绝不是那些离疟疾如此之近的非洲人民在说‘停止这项技术吧!’”
青蒿素还只是第一步,Keasling希望可以有更大规模的项目。“我们应该能够在微生物中合成任何一种我们想要的植物成分,”他说, “我们应当掌握所有的代谢途径。如果你需要这种药物:好的,我们提取这个部分,这一段。把它们放进微生物中,两个星期以后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产物。”
Amyris公司在发展新能源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青蒿素是一种烃类,我们构建了一个微生物的平台用以生产它,”Keasling 说。“我们可以去掉一些基因然后放入一个不同的基因,青蒿素就变成了生物燃料。”Amyris在John Melo(一位曾就职于英国石油公司的资深执行官)的带领下,已经制造出了三种可以把糖类转化为燃料的微生物。“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Keasling说。“我非常明白这让许多人焦虑担忧,也明白其中的原因。任何一种如此强大的新生事物,都意味着麻烦。但我不认为泥足于过去就可以给我们未来想要的答案。”
在最初的40亿年间,地球上的生命是完全按照自然的好恶成形的。在选择与几率事件的推动下,最高效的基因被保留下来,演化的过程使得他们得以繁衍欣欣向荣。漫长却绚丽的达尔文演化过程在不断的尝试与错误、挣扎与生存中缓缓前进,持续了千万年之久。然后在大约一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开始聚集为村庄,种植农作物,蓄养动物。石斧与织布机逐渐出现,并且帮助人们种出更好的庄稼,带来更丰富的食物来源,从而可以养活更多人。羊猪等家畜的繁殖逐渐让位于金属的冶炼和机器的制造。纵观整个过程,新生事物总是以其特有的力量横空出世,伴随着其他事物的黯淡失势。
到21世纪初,我们用分子生物学改造生命最小组成部分的能力已经如此之强,即便是对这种能力运用得最娴熟的人,也不敢声称自己完全了解这种力量。人类对于自然的掌控力已经在几个世纪前被预言――Bacon(培根)坚持相信这种控制力,而Black(布雷克,我想此处作者应是指 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国著名诗人,画家和雕塑家――译注)则表现出深深的畏惧。可是从孟德尔(Gregor Mendel,遗传学先驱)揭示出豌豆植株的遗传特征――包括植物的形状、大小还有种子的颜色等等――,以及它们一代一代的传承方式,从此使得这些特征可以被预测,被重复,被写入遗传定律,到现在仅有100年出头。
从那时开始,生物学的核心工作就变成了破译密码,并且学习解读密码――从而了解DNA到底是如何创造和延续生命的。生理学家 Jacque Loeb把生命的人工合成看做是生物学的目标。1912年,近代生物化学的奠基者之一Loeb,在文章中写到没有任何证据表示“人工制作活体物质在科学范围内不具备可能性,”并且声称,“我们要么成功完成生命物质的人工合成,要么必须找到行不通的原因。”
194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遗传学家Hermann J. Muller曾经做出过此类尝试。他通过展示活体细胞的基因和染色体可以在 X光的照射下发生变异,第一次证明了遗传原来可以被自然选择以外的其他因素所影响。但是他不确定人们是不是可以有责任感地利用这个信息。“如果我们掌握了这种知识和力量,毫无疑问最终我们一定会使用它,”Muller说。“人类是动物中最为狂妄自大的――他们看到高山就会努力建造出像高山一样的金字塔,如果他们看到演化这样一个伟大的进程,并且认为自己完全够格加入这种大自然的游戏,他们就会带着轻蔑不遗余力去尝试。”
生物演化理论解释说地球上的每一个物种都同其他物种有着某种联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遗有历史的记录。1953年,詹姆斯? 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 克里克(Francis Crick)通过揭示DNA的自身结构,使得解读这种历史记录成为了可能。这种语言只有4个化学字母――腺嘌呤,胞嘧啶,鸟嘌呤和胸腺嘧啶――以庞大的核苷酸链为形式。当它们被结合在一起,其序列就可以决定人类为何各有各样,并且与其他的生物也迥异不同。
到20世纪70年代,DNA重组技术已经使得科学家可以把长长的不便于使用的核酸分子切成易于使用的基因片段并且把他们粘贴进其他细胞当中。突然之间,研究者们居然可以将两种在自然中绝不可能相交的生物的基因连接在一起。尽管这种技术前景广阔,但它们又使得科学家们可以将病毒以及造成癌症的微生物,从一个生物中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中。这会造出没人可以预料到的新疾病,并且相应的没有任何天然的防御措施,治疗方法或者治愈的把握。1975 年,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聚集到了位于北加利福尼亚州Asilomar会议中心,商讨这项新技术所可能带来的危机与挑战。他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实验安全和环境安全,并得出结论这个新领域需要一些规章制度。(并没有任何真正关于蓄意滥用的讨论――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有讨论它的需要。)
当回忆起30年前的事情,当时的会议组织者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Paul Berg写道,“这次独一无二的会议,开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对科学而言如此,对科学政策的公开讨论亦如此。它的成功令在当时充满争议的DNA重组技术得以蓬勃发展。现在DNA重组技术在生物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问题的源泉,又是开启答案的钥匙。”
DNA解码工作曾经单调而冗长。一个科学家用整整一年,可能成果只有10或12个碱基对长度的片段。(我们的DNA由30亿对这样的碱基对组成。)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自动测序机大大简化了这个过程,而今天的仪器可以在几秒内就处理完信息。另一种新的工具――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最终将数字世界与生物世界真正结合在了一起。科学家可以使用PCR选择一个DNA分子并复制很多次,使之更容易操控和测序。这使得细胞对于科学家来说,变成了装载着以最简明方式排列的数字信息的复杂包裹。
研究者们用这些技术,让塔斯马尼亚虎――这种世界上最大的有袋食肉类动物,同时也是已经在70年前灭绝的动物――的DNA复活了。 2008年在墨尔本,来自墨尔本大学和位于美国休斯敦德克萨斯大学M.D.癌症中心的科学家们从一个保存于维多利亚博物馆的组织中提取出了DNA。他们将老虎体内负责编码胶原蛋白的基因片段提取出来并放入老鼠胚胎中。这些DNA启动了对应的基因,老鼠胚胎开始产出胶原蛋白。这标志着第一次成功让已灭绝生物的组织(病毒除外)在另一种生物体内正常运作。
这绝对不是最后一次。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小组一直致力于研究两只长毛猛犸的毛发样本――两只猛犸一头六万岁,一头八万岁――他们给出了一种尝试性的方案,来修改猛犸的DNA然后放入大象的卵子中。这样猛犸就可以被象妈妈生出来了。“毫无疑问看到一头活的,会呼吸的长毛猛犸多么令人雀跃――一个长满粗毛,长牙卷曲,令我们想到又大又圆的毛绒玩具,而不是吓人的霸王龙,”Times在得知这个发现后不久如是评论。“我们只是不确定猛犸是否也像我们一样开心。”
不过最终极的目标是创造出一个仅由化学物质和DNA蓝图构成的合成生物。在90年代中期,在基因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r Genomic Research)工作的Craig Venter,和他的同事Clyde Hutchison 以及Hamilton Smith开始思考他们能否将生命还原至它们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然后用这些基因重新造出这样的一个生物。他们开始修改一种叫做生殖道微浆菌(Mycoplasma genitalium)的小细菌的基因组,其中包含482个基因(人类有大约两万三千个基因)和58万个碱基对,它们都排列在一个环形的染色体上――这是已知实验室培养出的最小的染色体。之后Venter和他的同事将染色体上的基因一个一个去掉,试图找到可以维持其生命活性的最小基因组合。
Venter把这个实验叫做最小化基因组工程。到2008年初,他的小组已经制作出了数以千计的化学合成DNA片段,并把它们组装成了一个新版本的生物体。然后他们完全摆脱mycoplasma genitalium的基因组,仅用化学物质制造出了产物。“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方法,都不仅仅局限于合成DNA,”Venter在他那篇后来发表在Science上的工作报告里如此记录。“以自己想要的顺序组装出任意组合的人工或天然DNA,应该是可以实现的。”这也许是科学发展史上最轻描淡写的表述之一。接下来,Venter尝试把人造染色体作为一个“启动装置”植入另一个细胞的细胞壁中,因此而产生了一种可以自行复制DNA的新的生命形式――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造生物体。(积极分子们已经将这个新生命体命名为 Synthia。)Venter希望Synthia以及类似的产品可以在将来成为运载不同基因包裹的容器。比如说,一个包裹也许可以生产出一种特定的药品,而另一个包裹里的基因是为消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而设计的。
2007年理论物理学家Freeman Dyson在参观了在费城花卉展及圣地亚哥爬行动物展之后,在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写道“每一朵兰花或玫瑰,每一只蜥蜴或蛇,都是一位甘愿奉献自我而又熟稔培育技巧的培育者的心血。成千上万的人,不论业余的或者专业的,把他们的人生贡献给了这个行业。”当然,这也是我们在千百万年来一直做的事情,尽管方式可以不尽相同。“现在想象一下,如果基因工程的工具也到了这些培育者的手上,会发生什么。”
Dyson向我们描述了这样的场景:新生物种被创造出来,多种多样欣欣向荣……设计基因组将成为一种个人行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就如同绘画与雕刻。只有极少数的创作能够成为伟大的作品,但是很多的作品都给他们的创造者带来快乐,也使我们的动植物更加多样。”看来完全为人类所驾驭的生物技术将这个景象带到我们身边,只是时间问题。
生物技术游戏可以供“低至幼儿园年龄的小朋友们玩耍,他们要用真正的蛋和种子,”制造出全新的物种――比如云雀。“这些游戏可能一团乱甚至具有一定的危险性,”Dyson写道。“需要设定条例与规则来保证我们的孩子不会伤害到自己或者别人。这些生物科技的危险可是实实在在而严重的。”
地球上的生命是沿着弧线发展的――这个过程始于大爆炸,演化至一个聪明的毛头小子也可以从冷水鱼中提取基因,引入草莓中,以防止草莓被冻坏。你不必变成一个勒德分子(即反对新技术的人)――或者查尔斯王子,他的著名论调是这个世界将会在贪得无厌和失去控制的科技发展中变得一片灰暗――都会想象到,如果合成生物学取得了成功,那么可能我们创造的世界就会替代达尔文的演化构建出的这个世界。
“很多科技都会在某种情况下被认为是对上帝的冒犯,但也许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像合成生物学这样引发如此直接的控诉,”Nature的编辑――一群仍旧支持这项技术的人们――于2007年这样写道。“因为开天辟地第一次,上帝也有了竞争者。”
相关阅读:
- 农业部:进口转基因生物经严格评价可放心食用 (snwxf, 2012-4-20)
- 检科院举办输欧米制品转基因成分检测方法培训班 (snwxf, 2012-4-25)
- 转基因安全吗? (tang1986gdfs, 2012-5-11)
- 转基因在美国的遭际 (lian1982800, 2012-5-13)
- 英公众与科学家爆发“转基因冲突” (snwxf, 2012-5-23)
- 专家谈转基因技术:不能过分夸张也不能无视发展 (snwxf, 2012-5-23)
- 朱祯:态度和管理决定着转基因产业去从 (snwxf, 2012-5-25)
- 转基因小鼠制备实验 (liuzhikunwq, 2012-5-27)
- 陈君石:转基因不属于食品安全范畴 (snwxf, 2012-5-29)
TAG: 转基因
标题搜索
日历
|
|||||||||
| 日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
| 1 | 2 | 3 | 4 | 5 | 6 | ||||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
| 28 | 29 | 30 | |||||||
我的存档
数据统计
- 访问量: 1693
- 日志数: 16
- 建立时间: 2010-10-12
- 更新时间: 2012-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