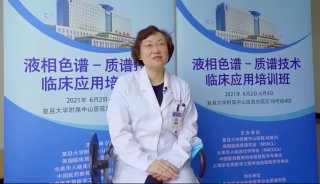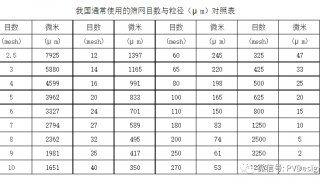医患关系中的“权力-知识”模式
著名哲学家和医学史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984年6月)的“微观权力说”认为,近代医院是一个按照“权力—知识”模式建构的空间。在现代医院空间中,医生使用“科学的话语”对病人的身体行使支配的权力,就像中世纪的僧侣代表上帝对信徒的灵魂实施控制一样,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中国近、现代影响最大的医疗纠纷案是“梁启超错割肾脏案”。1926年初,梁启超因血尿久治不愈而进入协和医院,医生经过包括X-光在内的一系列检查后认定他患有右肾肿瘤,并据此作出切除右肾的决定。手术于1926年3月16日实行,术后对切除的右肾进行病理检查,结果既没有发现肿瘤,也没有任何病灶。术后,医院立即意识到右肾是被误切了,又在口腔和饮食上找原因,拔去梁启超七颗牙齿,并饿了他好几天,结果仍止不住尿血。三年后,梁启超病逝。梁先生虽是社会名流,但是对医学却是外行。他自已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切,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梁案已广为人知,并曾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被赋于了福柯式的解读。俞凤宾的《饮冰七日记》,则通过一个医学名人因割治扁桃腺而进入医院的空间后的遭遇,提供了另一个福柯“权力—知识”模式的生动案例。
俞凤宾是沪上名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1923年起先后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教授,并兼任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俞凤宾是中华医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华医学会第三任会长,是当时中国医界的风云人物。俞氏早年曾患猩红热,1925年前后又频患扁桃腺炎,并由此而转变为慢性肾炎。因此,1928年前后俞氏遂有割除扁桃腺之意。于是经朋友介绍,进入一家大医院实施手术。据俞凤宾介绍:“此院规模宏大,建筑庄严。紫色大理石舗地……其中手术室,大小四、五间。楼凡五层,病房数十间,均属最新式之建筑,各有浴室并热气装置。电梯二副,服务人员均分日夜二班……平日雇用人员甚多,即一般看护,已达数十人,其中有英美俄丹诸籍。…该院每日之用度须五六百两以上。故头等病房虽收费一十四两,另加特别治疗等费…”(引号中文字均引自俞氏《饮冰七日记》原文,下同)。这突显了一种医院在空间上的震摄感。
1929年3月8日(阴历正月27日)上午七点半,患者俞凤宾被推入手术室。此时手术医师正在换衣洗手,手术开始后,医患相对而坐,医生一面手术,一面则对病人谈笑风生,半小时后手术即告完成。术后病人除略有噁心外,感觉尚好,便被推回病房。但回病房后不久,病人即开始频吐鲜血。上午十时左右,出现头晕,出冷汗,遵瞩含用冰块止血无效,乃唤看护让其电话告手术医生。但因医生正出门诊,不能来病房探视。到下午2点,病人出现头晕,出冷汗,呕吐并出现频繁吐血。乃再让看护电告手术医生。由于医生下午2-4点又为其出门诊时间,“看护佯言已告,阴实违抗不与通消息”,还责备病人“多咳多饮以至血液之喷呕”。下午3时开始,“血来如涌”,看护仍不愿电话医生,病人家属俞夫人要求使用电话也不允。“余不得已乃以满貯血质之盆,示看护,未已又示一盆”,此时看护紧张了,乃电告手术医生。然此时医生已下班,联系不上。而此时病人出血加剧,失血更多,“满头冷汗,双目昏花,四肢乏力。自知险象环生…彷佛束手待毙而己”。看护见此状,“乃始惊慌失措”,其中有一英格兰看护“狂奔下楼”,遇见该院另一医生,此人亦不知如何处置,见病人喷血不止,建议送手术室,“用全身麻醉,紮住血管”。旁边一人提醒,病人脉博细弱已几乎不可扪测,如何再行全身麻醉?“其时室内诸看护,及外来之医生,均慌乱异常,手足无措”。病人此时“颜上冷汗涔涔又下,复发晕一次。少顷睁眼一望,觉电火通明之室,如昏黑无光。不见人面,微闻人声。即人声亦惭听惭远,乃知去世之期迫近矣!”。及此,“又频呕血,盆不及受”。在此紧要关头,手术医生的一个同事(可能也是外科手术医生)因诊治另一病人到院,被看护叫来应急处理。他让病人张口观看扁桃体手术处,发现出血点在喉之左边,上有血块,乃拭去血块,病人“于恍惚之中,见其为余敷药,按之约二三分钟。”后听该医生讲,“血己停止,只需静养,再观其后”。此后,患者又呕吐少量紫黑色血液后,便不再出血。而手术主治医生赶到医院时,已晚上八点了。此时病人出血已止,“惟疲乏不堪,如患大病;自觉呼吸长短不匀,拇指震颤无定。乃大虚之一种现象。翌晨,自察手掌,呈惨白色,鸡皮皱襞,如七秩老翁”。
俞氏此次手术共住院七天,“七日之中之滋养料,均冰冷之物。因喉间受创后,惟冷液可入,热者必致大痛,故所饮者如冰水、冰桔汁、冰牛乳、冰淇淋、冰柠檬汁、冰鸡汤等”。据此,俞氏写一文详细记敍了此“索命”之经历,命题为“饮冰七日记”,载于《中华医学杂志》1929年第15卷第5期“艺文”栏中。俞氏原本已有慢性肾炎,经此折腾,病情迅速恶化,于1930年12月4日去世,年仅46岁。
俞氏此案中有几点颇需注意。其一,俞氏并无必需住院之病,仅因扁桃腺炎常发,欲去除病根,萌手术去除之意。做此决定前,俞氏不是沒有顾虑的。住院前,他曾为此咨询过数位中、外同行。中国同行都建议谨慎行事。洋医朋友则皆主张手术,称可施局部麻醉后,扁桃腺可“用箍钩术”去之。权衡之后,俞氏最终决定手术。但一旦进入医院这一空间,俞氏之“沪上名医”的身份便消失了:他只是一个将身体交付“手术医生”,割除扁桃腺的病人;其二,此医院实体的豪华气派以及雇用人员,病房设备之周全、包括收之高昂,俨然突显出一种宗教庙堂的神圣,让人产生震摄之下的敬畏和信任之感。这种震撼作用对作为病人的俞氏心理来讲,极为重要,因为他本人即是医界名人。其三,俞氏的术后出血不止,险象环生,并多次要求电告手术医生,而医护人员漠然视之,手术主治医生则完全置病人的险情不顾,迟至病人频繁出血10个小时后才现身临床。医院对一个“名医同行”患者的生命,竟会漠视到这种程度,似乎令人吃惊。但实际上,在医院这个“权力-知识”的空间里,任何病人,梁启超也好,俞凤宾也好,他们“病人”的身份都是一样的。在现代医院中,医学知识权力是全复盖的。任何人,不管你是何等人物,一旦进入医院的空间,便丧失了其社会学上的身份,而统一于生物学的属性,曰:病人。在这里,病人必需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身体,包括个人的行动自由、身体隐私和疾病的治疗方式都交由医生支配。
在梁案中,梁启超对错割右肾采取的是“接受”和“掩饰”的态度。据说是为了维护西方“科学的医学”(Scientific Medicine)的声誉。他发文写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但术后不到三年,梁启超在饱受病痛折磨中病逝。在俞案中,俞氏对这次险些丧命的医疗过程显然是极为不满的,以致在出院后即以“饮冰七日记”一文将其公开发表。但文中仍隐去了该医院和手术医师之名,可见医界规矩(福柯称之为“规训”)之威严。俞凤宾在其术后一年另九个月后因肾功能衰竭而病逝。
在医院的空间中,医者对患者的强势地位是勿用置疑的,为防止这种“知识权力”的滥用,在医学的起始,医界就通过道德的宣示,提出了对医者行为进行约束的各种“誓言”,其中最著名的是二千多年前,古希腊医界提出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誓言中明确宣示:“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这使医学成为一种最受尊重的神圣职业,甚至被看成是“现代神学”。但医疗实践毕竟是一种很实际的行为,医患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交换的关系,其基础对病人来讲是“信任”,对医者来讲是“尽责尽力”。病人进入医院以“性命相托”,以求医学对自已疾病的治愈。但这种交换在实际上又不可能对等的。对病人来讲,“信任”意味着给出自已的全部:身体及与此相关的生命的尊严;而医者的“尽责尽力”则不得不受限于医学发展的整体水平,主持治疗医生的治疗水平及责任心等多种因素。因此,病人就医就抱着“治愈疾病”的目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相反,疾病常常并不能治愈,有时甚至死亡。因此,“医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医学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100年间,医学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现代还原论医学对许多疾病的认识和治疗还处在“经验时期”,对许多“复杂性疾病”(如各种慢病)的发病机理还不完全清楚;临床医学对这些疾病的诊断、治疗还不甚理想。在相当长时间内,这仍将是一种“常态”。
当下中国医患关系紧张,有的已影响到医疗工作的正常开展。医患双方都颇有怨气,尤以患者为甚。福柯关于医患关系的“权力—知识”模式,虽然很直白,但却很深刻。它并没有对临床医疗结果作价值判断,它只是揭示了医-患之间的本质关系。一般来讲,没有病人会主动挑衅医生,而医生总是希望能治愈患者的疾病。因此,医患关系的和谐自有其内在的逻辑。但现代医学并不总能做得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对医者来说,固然有受医学发展水平限制的因素,但面对以“性命相托”的患者,切实地担负起一个医者的神圣职责,是十分重要的。而对求医者来说,深刻地理解医患之间关系的这种真实性质并正确地认识医学与疾病的关系,也是很有必要的。和谐的医患关系必需建立在真正相互理解的坚实基础之上,对此医患双方都要作出更多的努力。
-
精英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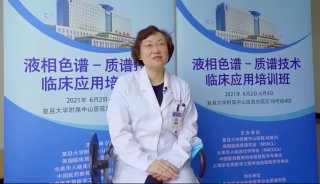
-
技术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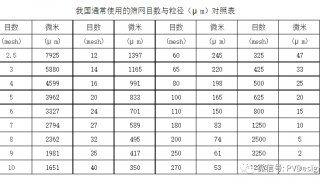
-
焦点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