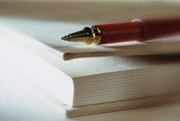本刊1988年第8期推出了常存库、刘兴旺的两篇文章,他们从“科学蒙难”角度剖析了中医体系拒绝“杂气学说”的种种原因,读后让人无限惋惜,似乎进化机制再多情一些,夭折的“杂气学说”会长成现代微生物学的大树,不同凡响的吴又可能成为中国的巴斯德。
真是这样吗?
一、他已经踩着了近代医学的门槛
就当时而言,杂气学说是十分“独特的”,它不约而同地孕育着与西方近似的“奇想”,这种奇想在西方带来了近代医学,在中国却没有落脚之地。从这一点看,我们说吴又可已经踩着了近代医学的门槛。
1.不自觉地摆脱着有机自然观
有机自然观是古代科学的基本特征,它对中医学的突出影响是使其人体观、生命观、疾病观、治疗观等人格化。自然化,即以自然现象、社会伦理来解释医疗事实的内在机制。吴又可的著作《温疫论》基本上避开了类似说法,他根据自己的体会,还对某些说法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他认为,杂气“不可以年月四时为拘”,亦“非五运六气所能定”,其“为病最多,然举世皆误认为六气”(《温疫论·杂气论》)。他对六气致疫提出异议,“夫寒热温凉,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微损益,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必多雨,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温疫论·原病》)。对这个问题,他从三方面进行剖析:其一,寒热温凉受风雨阴晴的影响,稍有变化是其常事,而且,温暖乃天地中和之气,能使万物发育,气血融合,不足为病(见《温疫论·诸家温疫正误》);其二,有时气候正常,却仍有疫疬流行则无法解释(见《温疫论·伤寒例正误》);其三,从疾病的反应说来,二三月或八九月天气温凉,亦有病重者大热不止,失治而死的;五六月气候炎热,亦有病轻热微,不药而愈者(同前条),不能简单对应。当然,吴氏批判“六气说”是为“杂气说”开辟市场,他不可能以我们今天的高度去认识有机自然观,也没有全面系统地考察中医学体系。
2.朦胧的“白箱化”要求
中医学虽在早期有过“白箱化”需求,后来由于文化背景的作用,一直热衷于经验的“黑箱调节”。吴又可在批判“伏寒说”时指出,“肌为肌表,肤为皮之浅者,其间一毫一窍,”岂是留邪之所?似乎有疾病定位的想法,但其“邪伏膜原说”又退回到思辨玄想的茫途。他对“何等中而即病?何等中而不即病?”反复设问,有穷究原委的理性思维倾向,他的“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的见解以及“莫知何物能制之”的感叹,对中医研究提出了要
“知物”的新要求。这代表吴氏朦胧的“白箱式”思维取向,与传统中医“援物比类”、“以象测脏”有较大的差异。
3.初步悟出“感觉比经典更可靠”
西方医学革命以维萨里向盖仑挑战,研究人体解剖,帕拉塞尔苏斯批判“四元液学说”,引进化学方法为起点,吴又可被认为“离经叛道”、“创异说以欺人”,也是因为他跳出了“注经”式著作方式,如王清任所称:“皆独出心裁,并未引古经一语。”他呼吁“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法,原无明论”,导致夭亡者“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力求对历代“温疫”之论以正时误。他相信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在此基础上总结的杂气说,把病原微生物的某些重要特性完全揭示了出来,如杂气的多样性、特异性定位和种属感受性等等,特别是与外科感染性疾病联系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问题是他无法迈出关键的两步
要跨入近代医学的殿堂,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构造性自然观,二是受控实验。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因而近代科学包括近代医学也就没有在中国产生。
的确,任何杰出的人物,任何超脱的思想,总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与其身后的文化背景休戚相关。翻开《温疫论》,那种闪灼着东方传统的思维方式跃然纸上。吴氏对于他所孜孜以求的“杂气”也表现出“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的洒脱风格。他虽然在与温疫作斗争的长期临床过程中,总结了许多杂气致病的特点和规律,但从方法学上并没有跳出“六淫外感说”的朴素“本体论”模式,因为杂气毕竟是“直观合理外推”的产物,他没有想到要去证实自己的想法,也不知道该怎么证实。然而,当吴又可主观地认为杂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以“不可知”的神秘色彩草率了结之后不久,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就已经开始在显微镜下研究一个微小的新世界。那么,如果此时有一架显微镜,吴氏是否会成为中国的巴斯德呢?人们一定会抱怨,科学发现寓寄了太多的偶然性,我们的祖先很早就通过控制窖内温度和氧化还原时间来制造瓷器,却一直没想到用它来制造玻璃,而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哲学家Seneca就发现,“无论怎样小和难以辨认的字母,都能通过装满水的玻璃球或玻璃杯放大而看得更清楚。”其实,这种抱怨大可不必。要知道,当时的吴又可能否就把显微镜下的生物与神秘的“杂气”挂上钩呢(这种联系在西方也延搁了近两个世纪)?他能够把我们最陌生的受控实验运用于杂气的研究中吗?既然如此,那种“莫知何物能制之”的感叹和希冀就只能永远停留在传统医学的史册上。
其次是重实用轻理性的传统。我们可以看出,同绝大多数古代医籍相似,《温疫论》中没有逻辑型结构体系,除“源病”、“杂气论”、“论气盛衰”、“论气所伤不同”等极少数几篇中,以一种挟叙挟议的手法阐述自己的理论见解外,其余90%以上篇幅均是临床用药的经验体会。由于传统文化的“重用轻理”倾向和形式逻辑的欠缺,吴氏《温疫论》中的杂气学说也显得含混零乱。其一是概念不清,没有严格定义和划分的意识。就连其最重要的概念——“杂气”,既没有具体确切的内涵,也没有层次分明的外延。其二是理性程度低,缺少必要的科学抽象。因为“重用轻理”,对于事物规律的形式研究,吴氏同样无法深入,再加上归纳、演绎等逻辑方法的缺憾,仅采用挟叙挟议方式,用具体的事例代替理论陈述以及事物规律的抽象,则无法构成严密的公理化体系。其三是可控实验的无知,不能实现对理论的鉴别和清晰化作用。
基于上述,要使杂气学说发展成为现代微生物学,有着难以逾越的巨大屏障。
三、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启示
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历史反衬着现实。中医学体系为什么要排斥杂气学说?杂气学说为什么不能成长为现代微生物学?这些问题既是事实,又发人深省。的确,微生物学和近代医学的发现权已经属于了别人,但科学是全人类的,如果我们中医要走向世界,对现代科学做出贡献,就必须认清自己的现实,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张开新的视角。因此,笔者认为:
1.突破“中体西用”,更新科学观念
“中体西用”是我国近代以来的学术思潮之一。为了发展中医,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率勤跋涉,几更旗号,先后经历了“中西医汇通”、“国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多学科研究”等多种形式,为什么最终要退回到“保持特色”的境地上呢?“中西医结合”为什么能在应用上时有建树,理论上结合却不伦不类、貌合神离呢?为什么与中医学有着共同基础的传统科学都不能“中体西用”,却只能改弦易辙?中医学能保留至今,是因为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还是因为颇有实用的临床疗效呢?我们在自然哲学的“迷宫”里已经耽误得太久,儒家的“合理外推”,道家的“神秘主义”,以及“烦琐考证”、“重用轻理”传统,已把我们捆绑得够苦,我们今天首要的是思想觉醒,突破“中体西用”,更新科学观念。
2.抓住经验事实,探讨具体机制
医疗事实一旦被确认是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我们就要广泛搜集中医各科临床的经验信息,尤其是现代难治疾病的多种疗法。不仅从汗牛充栋的古代医籍、现代期刊文献中,还要从经验的活载体——名老中医和民间草医中搜集。我们的原则是:搜集要广,分类要精,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然后遵循正确的科研程序,严格地把握样本大小、对象选择、对照设置、指标制定、资料分析等原则,有效地开展临床研究。在前人基础上(包括以理论形式存在的经验事实),进一步取得有代表性、可比性、精确性、可重复性的资料和数据,以期得出客观的结论和解释。同时,密切配合基础研究,提出假说,设计实验,形成“理论<=>实验”、“应用研究<=>基础研究”的双重大循环。我们坚信,中医事实以一个个新理论的面貌出现之日,就是中医升华为未来科学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