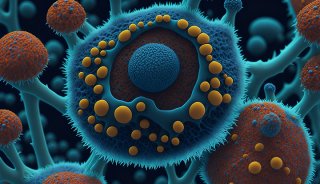肠道糖基化在维护肠道微生物稳态中的作用
人类肠道中含有极其丰富的微生物,其所含基因总数是人类基因组的150余倍。这些微生物通过相互竞争、互补和协同,构成了微生物-微生物和微生物-宿主关系的复杂网络。在此基础上,肠道微生物各组分间相对平衡,保持稳态,从而实现其与宿主互利共生。对于宿主,其肠道内存在多种屏障以维持肠内微生物的稳态。其中包括:胃肠道表面由紧密连接而连接起来的肠细胞和杯状细胞等分泌的黏液层组成的机械屏障,上皮细胞产生抗微生物肽等物质组成的化学屏障,肠道内定植益生和共生细菌组成的生物屏障,机体先天性免疫系统和获得性免疫系统构成的免疫屏障。以上多种肠道屏障是一个有机协同的整体,由此建立起宿主与非致病微生物的良性共生,奠定了正常肠道功能的重要基础。

肠道中宿主-微生物相互调控下的共生关系对肠道微生物稳态和正常功能的维持十分重要,因此有可能是肠道稳态失调和相关疾病治疗的一个切入点。近期研究发现,肠上皮聚糖在宿主-微生物相互作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肠道的糖基化在调控微生物的同时也受微生物刺激和肠道免疫系统调节。在此着重回顾肠道糖基化,特别是α1,2-岩藻糖糖基化作为宿主-微生物交叉调控的生理和免疫学机制,寻找新发现的与临床肠道疾病的可能关系,并为肠道动力相关疾病的诊治拓宽思路。
一、肠道糖基化与宿主-肠道菌群调控
在活细胞中,细胞表面蛋白质和脂质在特定酶催化下被多糖修饰,形成相应糖基,从而表现出多样的生物化学功能。肠上皮细胞表面表达和分泌的糖基具有独特的功能特征。一方面,肠道腔面的糖蛋白和糖脂可作为宿主和管腔微生物之间通讯的重要媒介。例如副溶血性弧菌通过硫酸化和岩藻糖化聚糖靶定相应的上皮细胞上相关生物转化分子,从而感染宿主细胞[1]。另一方面,微生物产物也可由上皮的糖基介导产生作用,如霍乱毒素与肠道上皮表面的GM1神经节苷脂间的相互作用。在众多肠道糖基化类型中,岩藻糖基化的功能最受关注,相关研究最深入。岩藻糖基化反应由岩藻糖基转移酶(fucosyl transferase,FUT)介导。在人和小鼠肠道,FUT2作为主要的岩藻糖基转移酶,特异性表达和调节肠上皮细胞和杯状细胞上的α1,2-岩藻糖基化。由FUT2介导合成的糖基化抗原常被分泌至口腔和肠腔内,因而FUT2也被称为分泌型基因(secretor gene)。α1,2-岩藻糖在肠道上皮表面表达和以分泌型糖基在肠腔内表达极大地增加了其与肠道微生物接触的机会,也形成了其介导宿主-微生物相互调控的基础。
二、肠道糖基化对肠道菌群的影响与机制
肠道中的多类共生菌可利用肠道上皮表达的糖基,如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就可产生岩藻糖苷酶以从上皮细胞上切割α1,2-岩藻糖并加以摄入。摄入的L-岩藻糖可被分解代谢作为碳源和供能,或用于调控岩藻糖操纵子基因,或被再循环作为岩藻糖化的荚膜多糖的原料。研究表明,上皮α1,2-岩藻糖合成缺陷的脆弱拟杆菌较野生型存在明显的竞争劣势,而FUT2缺陷小鼠往往具有肠道微生物紊乱,可加剧柠檬酸杆菌诱导的肠道炎症和功能障碍。可见α1,2-岩藻糖在肠道内有助于维持宿主-微生物共生和肠道微环境的稳定。此外,也有研究表明,肠腔游离的L-岩藻糖可通过激活岩藻糖感受器FusKR43抑制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毒力基因的表达[2],这提示上皮α1,2-岩藻糖基化可下调肠道致病微生物的毒力并对机体起到保护作用。
三、肠道菌群对肠道糖基化的诱导与机制
现有研究表明,葡聚糖硫酸钠等引起上皮屏障的功能障碍化学物质可诱导上皮细胞表面的FUT2和α1,2-岩藻糖的表达,这提示肠道屏障破坏可诱发上皮α1,2-岩藻糖基化。进一步研究发现,无菌小鼠在肠道上皮α1,2-岩藻糖表达受损,并可通过共生微生物定植而恢复[3],这进一步提示肠道微生物对宿主肠道的定植可诱导上皮α1,2-岩藻糖基化过程。实际上,现有研究已证明脆弱类杆菌和分段丝状细菌有此诱导能力。现有研究已对细菌诱导肠上皮糖基化机制做出诸多探索。首先,TLR激动剂可诱导上皮α1,2-岩藻糖基化,提示TLR途径参与微生物对α1,2-岩藻糖的诱导;其次,现在尚未发现不能附着于肠道上皮的微生物可诱导盐藻糖基化,提示诱导过程可能需要宿主与细菌配体信号直接结合;而与岩藻糖代谢途径有关的基因缺陷的拟杆菌突变体不能诱导上皮FUT2表达,提示细菌自身代谢参与上皮α1,2-岩藻糖基化的诱导。
除微生物直接作用外,免疫细胞也参与了肠道菌群对上皮α1,2-岩藻糖基化的诱导过程。研究表明,先天型黏膜免疫细胞是诱导上皮α1,2-岩藻糖基化所必需的。基于现有研究,来自3型天然淋巴细胞(group 3 innate lymphoid cells, ILC3)产生的IL-22信号可由肠上皮细胞特异性表达IL-22受体接受,并通过上皮细胞的IL-22受体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蛋白(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途径最终激活FUT2和其他防御基因的表达[4]。同时,获得性免疫细胞也在肠道上皮糖基化过程中起作用。根据现有研究,获得性免疫细胞与先天性免疫细胞的作用相反,可负向调节上皮FUT2表达和α1,2-岩藻糖基化[5]。表达IL-10调节性T细胞可能是获得性免疫细胞抑制上皮α1,2-岩藻糖基化作用中的关键。而在获得性免疫缺陷小鼠中观察到ILC3增加和IL-22的表达增加,进一步提示其机制涉及T淋巴细胞负调节ILC3数量和相应IL-22信号的产生。最终从肠道稳态的整体上考虑,在获得性免疫缺陷的情况下,上皮α1,2-岩藻糖基化的增强可进一步说明肠道上皮糖基化可能作为一种防御手段,在肠道功能缺陷时起到维护肠道微生物稳态的作用。
四、肠内多糖在肠道动力障碍临床应用的前景
肠道动力相关疾病的病因复杂多样,肠道微生态紊乱是诸多病因中无法忽视的组成部分[6],如小肠细菌过度生长与腹痛、腹胀、腹泻等肠道动力障碍表现密切相关。现有研究提示,其机制与肠道菌群紊乱所导致的肠道轻度炎症和内脏敏感性增高相关。肠道多糖可能通过对致病性和机会性微生物的抑制调节,发挥相应的防治效果。在肠道菌群紊乱时,肠上皮糖基化对各种病原体具有相对特异的抑制功能。如相对于野生型,鼠伤寒沙门菌等致病菌可更有效地感染FUT2缺陷小鼠。其可能机制为,共生菌通过定植竞争抑制致病菌增殖,从而维持肠道环境的稳态;上皮α1,2-岩藻糖可以直接抑制致病菌感染并下调其毒力;上皮的糖基直接干扰某些致病菌与肠上皮的结合定植。同时,实验证明服用含有α1,2-岩藻糖的牛奶可有效地保护宿主免受空肠弯曲杆菌感染,这进一步印证了肠内多糖对宿主的保护作用。
已有多项研究对通过调节肠内多糖水平改善肠道动力障碍做出探索。在一项研究中,菊粉型果聚糖显示出对实验对象肠道的免疫调节效应,同时增加了肠血液流量、摄氧量并改善肠上皮完整性,提示多糖对于肠道疾病治疗的价值。在IBS患者中进行的一项临床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摄入半乳糖基转移低聚糖(一类多糖)的患者在治疗4周后其粪便稠度、胃肠胀气、腹胀、复合症状评分和主观整体评估方面均获得了显著改善[7]。另一项研究显示,与安慰剂组相比,IBS患者摄入低聚果糖6周可降低消化道症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改善肠道不适和生命质量。尽管前途光明,但路途难免坎坷。肠道糖基化水平受肠道微生物和宿主自身的双重调控,同时肠道糖基化水平在部位时间上的差异性,均提示肠道多糖的保护作用可能随着宿主和微生物的改变而产生巨大变化。实际上,以口服多糖治疗IBS的相关临床研究为例,其治疗结果因研究对象、摄入糖的组成和剂量不同而有很大差异[7,8]。尽管如此,现有肠道糖基化研究已为包括肠道动力障碍在内的肠道疾病的诊治提供了新的前进方向,而未来对其机制的加深理解将为相关疾病的防治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