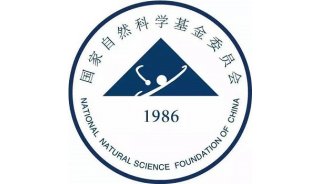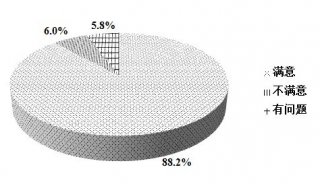郝刘祥: 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现代思考
原文地址: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3/8/506370.shtm
编者按
在“科玄新论”第一期,本报记者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郝刘祥、学术所长刘闯、学术委员会主任胡志强展开了一场对谈,对谈中学者们提出要“让‘玄学’为科学家开脑洞”。这里的“玄学”即形而上学。让形而上学,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为科学家开脑洞,首先要了解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对世界本原进行探讨,如何讨论宇宙论和本体论的。
本期专栏文章中,郝刘祥对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中最重要的3个概念——道、理和心进行了概念本意及现代意义的梳理。同时,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与西方哲学并无多大的差异;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通过合理的诠释和重构,完全能够融入现代思想体系之中。
■郝刘祥
形而上学,作为metaphysics的中译名,是明治时期日本哲学家根据《易经·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翻译而来。形而上学包括宇宙论(cosmology)和本体论(ontology)两个部分,其中宇宙论探讨的是宇宙的本原,即宇宙中的万物从何而来的问题;本体论探讨的是存在本身的结构,特别是超越感官经验的对象的存在性问题,比如共相(数、三角形、白、美、正义)、自然类(实体性共相,比如马)、自然规律(共相之间的必然联系)、神等是否真实存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宇宙论先于本体论,因为从神话时代走向理性时代,人们首先要追问的就是宇宙万物的由来。
按照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公元前600至300年,人类文明进入了重大的理性觉醒时代,即所谓“轴心时代”。此间在北纬30度附近形成了三大“轴心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国的先秦文明。理性觉醒的标志就是排除超自然因(神的干预),只用自然因来解释万物的由来和各种神奇的自然现象。这就是宇宙论兴起的背景。
宇宙论发展为本体论,主要是回答“变化问题”,即不管你假设宇宙初始是何物,抽象的也好具象的也好,都必须解释该物是如何变化成现今宇宙中的万物的。《易》尽管是一部卜筮之书,但其书名却是关于变化的,所以战国时期人们借题发挥为《易传》,使之俨然成为一部宇宙论和形而上学的著作。
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有3个概念——道、理和心。这些概念,在我们今天的思想和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日常对话中,我们经常会听到道德、天理、良心之类的说法。因此,对这些概念的本意及其现代意义进行一番梳理,确有必要。
笔者非中国哲学史专家,只是参照文本和已有解读——特别是钱穆的《朱子学提纲》谈谈自己的理解。
道
古代宇宙论的启发价值,就在于今人的创造性解读。
道的原意是道路,后来又有言说的意思,因此有人将其对应于希腊哲学的“逻各斯”。“逻各斯”的本意是言说,后来引申为说话的规则,进一步引申为一般性的规则。所以说,这种对应是不太准确的。道路之道,用来概括事物运动变化的轨迹,并不必然含有规则、法则之意。在古人眼中,天(日月五星)的运行,有常(规律性)也有异(如行星的留退)。自然的运行具有规律的信念,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结果。
“道”是老子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显然,老子的道不具备自然运行的法则的含义。《老子》一书,向来以晦涩难解著称。其实,只要我们跳过开篇的“道可道,非常道”那一段,很容易把握老子所指的“道”是什么。质言之,“道”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母体。兹引证如下: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意是:道是先于天地的存在物,是天地万物的母体,无声无形,循环运行不止)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大意是:道是生养万物的不朽谷神,是天地的玄妙母体,本身绵延不绝)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大意是:道虚而无形,先于一切有形质的事物而存在)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大意是:道是超感官的对象,看不见、听不到、摸不得。作为无定形的恍惚存在,道不可名状,无论根据什么都难以给它命名)
道常无名。(大意是:道难以用感觉属性来命名)
从上可见,老子的道是一个宇宙论概念,而不是一个本体论概念。如果我们要在西方哲学中找一个对应词,最恰当的莫过于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即没有确定形式或性质的万物之始基。
作为古希腊思想家泰勒斯的弟子,阿那克西曼德也在追问宇宙的本原。但他不同意泰勒斯水是世界的本原的说法,如果水是世界的本原,火又是如何来的?因此,他认为,宇宙的本原必定是一种不同于宇宙中所有事物的无定形的、未分化的物质。像“无定”一样,“道”虽“无名”,但绝不是“无”,而是不可名状的“有”,是生成万物的母体。
既然道是生养万物的母体,它是如何生养的呢?老子只拈出“自然”二字,所谓“道法自然”。大道泛行,无所不至,万物恃之而生、依之而养,并复归于兹,万物的生灭皆是“自化”。
这个解释当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所以千载之后,北宋的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观点:作为万物本原的“太虚”就是气,气的聚散浮沉形成了天地万物。张载的观点非常接近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第三代传人阿那克西美尼的说法。
明白了老子所指的“道”,回过头来就不难理解《老子》开篇之辞:“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据学者尹志华《北宋〈老子〉注研究》考订,宋代以前对这句话主要有3种不同的诠释:
(1) 道若可以言说,就不是恒常不变之道。代表人物是王弼。
(2) 道可以言说,但不是常人所言之道。代表人物是司马光。
(3) 道可以言说,但不是恒常不变之道。代表人物是唐玄宗。
随着马王堆帛书本的出土,第一种解释已逐渐失去了市场。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道篇》首句作:“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东汉之前汉语中没有系动词“是”,“……者……也”即表示判断,而非虚拟。正如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所言,“道”若是不可言说,老子又何必说那么多呢?
第二种解释与第三种解释差异在对“恒”或“常”的理解。老子所言之“道”,确实不是“常人之所谓道”,但将“恒”理解为“通常”确实有些牵强。作为天地万物的母体,“道”绵延不绝、周行不殆,并且生化万物,不仅不是不变的,而且变化的方式还千差万别。
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对此说得最清楚:
道者,虚极妙本之强名也,训通,训径……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万物,是万物之由径,可称为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无定方,强为之名,不可遍举,故或大、或逝,或远、或近,是不常于一道也。故云非常道。
古代的宇宙论并不只有历史价值。万物的本原问题,如今已成为物理学(特别是基本粒子物理学和宇宙学)的研究对象。事实上,不少量子物理学家都偏爱老庄的哲学,其中最突出的是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
汤川坦言,老庄思想始终潜藏在他的潜意识之中,影响着他对物理学理论的反思。比如,他将老子的“道可道”解释为“真正的道,即自然法则,不是惯常的道,或常识性的法则;真正的名称或概念,不是惯常的名称或概念”。再比如,他将庄子的混沌寓言解读为“最基本的物质没有确定的形式,同时具有分化成各种基本粒子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将老子的“道”诠释为量子场的真空态。古代宇宙论的启发价值,就在于今人的创造性解读。
理
朱熹对自然界的变化保持着极大的兴趣。他曾于高山上发现螺蚌化石而推之地球史上发生过沧海桑田的变迁;他还基于气的运行推断地居于宇宙中央而不是天之下,日月星辰分层布列于外周环运转,月之圆缺乃地球遮蔽日光之故。
与老子的“道”相比,朱熹的“理”是一个真正的本体论概念。理学在宋代又称“道学”,不过这里的“道”不是老子的“道”,而是儒家《易传》中的“道”,即阴阳变化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朱熹摈弃了前贤的太极与阴阳这两个用语,改用“理与气”这两个新词解释宇宙变化,是中国形而上学史上的一大创举。宇宙论催生了变化问题,本体论则要解答变化问题。
朱熹论宇宙万物本体,必兼言理气。宇宙万物中的生成与变化,都是“理与气”共同造就的,两者须臾不可分离。引用朱子的说法:
理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未尝离乎气。
如果我们要在西方哲学中找对应,最恰当的莫过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形式与质料”。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脱胎于柏拉图的共相理论。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我们要区分两个世界,即变化的世界(感官经验所能觉察的世界)和不变的世界(只有理性才能把握的世界),前者是现象,后者才是本体。本体世界中的各种共相(universals),比如数、三角形、圆、美、正义等,才是最基本的存在。这些共相都是超越时空的,感官只能看到这些共相的个例,比如某个直角三角形、某个美人等。经验世界中的具体事物,不过是这些共相的摹本。柏拉图的共相论,可以说颠覆了我们的常识。按我们的常识,所谓的共相不过是些抽象名词,是我们从经验中概括总结出来的。
柏拉图这一颠覆常识之举,为人类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共相犹如思想之“锚”,据此可以建立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概念框架。按柏拉图的思想,我们是先有正义本身,然后才有各种正义的行动。类似地,我们先有圆本身,然后才观察到各种近似的圆。特别是,行星不规则的视运动(特别是留退运动)本质上是圆周运动的组合。基于这一思想,希腊人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门理论科学——数学天文学,其终极形式就是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17世纪牛顿力学的创立,可以说是这一理论体系发展的自然结果。
柏拉图的共相论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共相到底是如何关联并影响到个体事物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分沾说(个体事物分沾了共相)不过是“说空话,打诗意的比方”。
其实柏拉图也意识到了自己学说的困难。在其晚年的著作《蒂迈欧篇》中提出,宇宙中的万物都是共相与“载体”(receptacle)的结合,这里的“载体”承自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未分化的初始物质。正如朱熹用“理与气”取代了此前的“太极与阴阳”一样,亚里士多德用“形式与质料”取代了柏拉图的“共相与载体”。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宇宙万物都是“形式与质料”的结合,形式(除了作为纯粹形式的上帝)不能离开质料而独立存在。
将朱熹与亚里士多德进行比较,并不是为了分出孰优孰劣或孰先孰后,而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他们的观点。
先说“气与质料”。朱熹的“气”,显然不是张载所说的“气”。张载的“气”是具象的,与之相比,朱熹的“气”是抽象的,更接近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概念,而不是其理论中的4种基本实体(水土气火)之一。
次言“理与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是一个事物之所以是该事物的原因。这与理的含义可以说别无二致。借用王夫之的说法,“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
将朱熹的“理”理解为“自然规律”(laws of nature),似乎有“过度诠释”之嫌。更恰当的诠释,应该是“自然类”(natural kinds)的概念,即一个事物之所以是该事物的缘由。“物之固然”,即事物的本质属性。比如,人有仁义礼智之四端,或按西方的说法,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事之所以然”,可以解释为事物的本质属性所导致的结果。比如,一颗种子在适合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会发育成杨树,是因为它携带有杨树的基因。
自然类与自然规律当然是有联系的,但两者不是一回事。从动植物分类学的兴起,到进化论和遗传学的建立,人类走过了漫长的旅程。当然,“事之所以然”也可以理解为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因”。从这个角度看,将“理”诠释为自然规律,也不算特别牵强。
关于“理与气”的关系,朱熹认为,“理”在“气”先,“理”可以先于物而存在: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
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
在物上看,则二者混沦不可分开。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未尝实有是物。
如果我们将朱熹的“理”理解为自然规律,那么上述引文可以解读为:自然规律先于自然过程。这也正是当今科学界和哲学界的主流观点,即规律适用于反事实的情形。
朱熹对自然界的变化保持着极大的兴趣。他曾于高山上发现螺蚌化石而推之地球史上发生过沧海桑田的变迁;他还基于“气”的运行推断地居于宇宙中央而不是天之下,日月星辰分层布列于外周环运转,月之圆缺乃地球遮蔽日光之故。
遗憾的是,宋之后中国人对自然的兴趣有限,天算家和本草家的目标也不是探究自然之理。但只要我们将“理”诠释为自然规律和自然类,朱熹的思想并不过时。自然科学的目标,就是要发现自然类和自然规律。所有的诺奖得主,不是发现了新的自然种类,就是发现了新的自然规律或机制。
朱子的“理”,除了可以诠释为自然规律和自然类外,还可以诠释为“自然法”(natural laws)。朱熹认为,“性即理也”,性是禀赋于人物之中的天理。朱熹对人性的认识受限于儒家的思想,片面强调人性中的善端,并且想当然地将“忠君孝亲”之类的伦理规范看成是“仁义礼智”的逻辑后承。尽管朱熹的“天理”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自然法”实质内容大异其趣,但两者都是“心之所有之理”。
心
假若我们接受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主张,将真理和公平作为首要之善或美德,将会给出全然不同的心学。
在朱子的学说中,心不过是“气之灵”。作为理的“能觉者”,心只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其本身没有本体论地位。南宋陆九渊提出了“心即理也”的命题,不过该命题中的“心”特指“本心”,也就是朱熹所言的心中之理,特别是心中的道德原则。陆氏虽然在早年就写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名句,但他既不否认作为五官之尊的心,也不否认充塞宇宙之理。相对于朱熹,陆九渊只是更强调人伦之理。
与朱熹甚至陆九渊不同,明代王阳明所求之理,单指道德原则(特别是儒家的伦理规范),与自然之理完全无关。王阳明格竹与朱熹观笋,可谓相映成趣。朱熹曾听道人说,竹笋只在夜间生长,遂在僧舍验之,插杆以记,发现竹笋日夜俱长。王阳明庭前格竹,试图通过观察竹子来获知做圣人的道理,不仅一无所得,反而劳思致疾。
王阳明的龙场顿悟,即感悟到圣人之道只在心中,无须外求。《传习录》载有王阳明与弟子徐爱的对话: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这里的理,指的是儒家的忠孝伦理;这里的事,指的是忠君孝亲之事。所以,心外无事与心外无理是同一个意思。
从“心外无事”出发,王阳明进一步断言“心外无物”。这里的物,指的也是行事。不过,所行之事不仅包括符合儒家伦理之行为,还包括视言动听这类人的一般行为。
《传习录》中,王阳明答爱问时说: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更进一步,王阳明将“心外无物”之物从意向行为推及意向对象。《传习录》载: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这里,王阳明似乎将作为道德本原之心提升为唯一的形而上学实体,外部事物不过是心的意向对象。
王阳明在儒家的地位,大抵相当于禅宗在佛家的地位。从学理的角度来看,王阳明的心学面临着两个非常大的困难。其一,“心外无物”的论点,有滑向唯心主义泥潭的危险;其二,王阳明强调,本心或良知是分辨“是非善恶”之心,但是非善恶的标准却是儒家的“忠孝仁义”。如此一来,既有的社会规范竟然成了先验的道德原则。
-
焦点事件

-
焦点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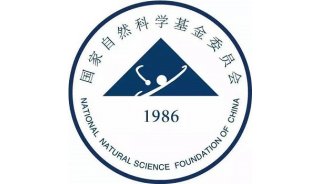
-
焦点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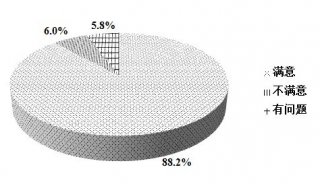
-
焦点事件